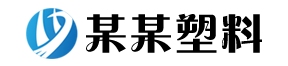“姑妈,我考研初试成绩出来了……”我攥着手机,心跳如鼓。“嗯,学院官网会发通知,耐心等。”裴雪鸿的声音平淡,门锁的咔哒声却像重锤敲在我心上。
过去一年,每个周六我都准时出现在她家,从客厅到书房,从书架到地板,每一寸都留下我擦拭的痕迹。

屏幕上的数字卡在三百六十七,比去年北城理工大学环境学院的复试线低两分。我盯着看了很久,久到手机自动熄屏,黑色屏幕上倒映出我那张没什么血色的脸。
“看见没?”我爸苏建国的声音从听筒里钻出来,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电流杂音,“你裴雪鸿姑妈在北理大当院长,就住学校家属院。你每周六过去,帮着收拾收拾屋子。”
“要什么要?”他打断我,语气里那种熟悉的焦躁升了上来,“她是你姑妈!你勤快点,多走动走动。她手指缝里漏点消息,够你少走多少弯路?”
“有什么不合适?”他的声音又拔高了一度,“你知道多少人想攀这层关系攀不上吗?”
裴雪鸿确实是我姑妈,但关系远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她是我爸的表姐,我总共只见过她两面。一次是我十岁那年,她回老家参加什么学术会议,顺路来看了一眼。她穿一件米白色针织衫,站在我家门口的水泥地上,鞋边沾了点灰。我妈端茶出来,她接过去时说了声谢谢,声音很轻。第二次是我大二,她来我们学校讲座。我挤在礼堂最后一排,看投影幕布上她的简介——一长串头衔里,“长江学者”和“国家杰出青年基金”这几个字格外刺眼。
那天晚上我爸喝了点酒,拍着桌子说:“看见没?这就是你姑妈!咱们苏家出的凤凰!”
血缘其实已经很淡了。裴雪鸿的父亲和我爷爷是堂兄弟,到了我们这代,基本就是过年群发祝福短信的关系。可在我爸心里,这层关系重得像座山。
“地址你存好。”我爸在电话那头说,“这周六就开始去。你裴姑妈忙,你去干活儿,别添乱,眼睛放亮一点。”
我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,床板很硬,硌得腿麻。窗外是北城四月的黄昏,天空泛着脏兮兮的橘红色。合租的室友在厨房炒菜,油烟味顺着门缝钻进来。
这是栋六层的老楼,红砖墙面爬满了枯萎的爬山虎藤蔓。三单元的门禁系统坏了,单元门虚掩着。我上到四楼,对着401的门牌深呼吸三次,才按响门铃。
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,短发,戴一副细边眼镜,穿着浅灰色的家居服。“是苏晚吧?”她侧身让我进去,“裴老师交代过了,你叫我陈姐就行。”
玄关很窄,地上摆着两双拖鞋。一双深棕色皮质的,鞋头有些磨损。另一双是崭新的浅蓝色棉拖鞋,标签还没拆。陈姐把那双新的推到我脚边:“穿这双。裴老师让你主要打扫客厅、餐厅、厨房,还有客卫。书房和卧室不用进去。”
房子比我想象的小。两室一厅,大约八十平米。客厅的沙发是布艺的,已经洗得有些发白。茶几上堆着几本摊开的期刊,最上面那本的封面印着英文单词“Ecology”。书架占满了一整面墙,塞得满满当当,一些书横着架在竖排的书上。
“抹布和清洁剂在阳台。”陈姐指了指方向,“拖把在卫生间门后。你先擦家具,最后拖地。”
她说完就进了靠里的那个房间,关上了门。后来我知道那是书房,裴雪鸿在家时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里面。
灰尘比想象中多。书架顶上积了薄薄一层灰,手指抹过去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。茶几上的期刊得一本本挪开,擦干净桌面再原样摆回去。摆回去时我瞥了一眼翻开的那页,满篇的曲线图和方程式,标题里有个词我认识——“湿地修复”。
裴雪鸿走出来。她穿着深蓝色的毛衣,袖口挽到小臂。头发比几年前白了不少,在脑后松松地绾了个髻。她看了我一眼,点了下头:“来了。”
“嗯。”她径直走向厨房,打开冰箱拿了瓶矿泉水,拧的时候手滑了一下。我这才注意到她右手的手指有些不太自然的弯曲。她换了左手,用力拧开瓶盖,喝了两口,又转身回了书房。
那天了三个小时。擦完所有家具,拖了两遍地,把垃圾袋拎到楼下。陈姐在我走之前递过来一个信封:“裴老师交代的,劳务费。”
“每周六上午九点到十二点,时间你自己掌握,干完就能走。”陈姐送我到门口,“下周来之前给我发个消息,万一裴老师临时有事。”
我渐渐摸清了规律。裴雪鸿通常周六上午都在家,但她几乎不出书房。偶尔出来接水或者去卫生间,也是步履匆匆。我们碰面时她会点个头,有时候说声“来了”,有时候什么都不说。
陈姐告诉我,裴雪鸿带的科研团队有二十几个人,除了上课,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。周六上午是她在家处理邮件和写材料的时间。
“裴老师手不太方便。”有一次陈姐闲聊时说,“年轻时候做野外采样,冬天在湿地待太久,落下了风湿。后来又常年用显微镜,手指关节都变形了。”
房子不大,但打扫起来并不轻松。裴雪鸿的书太多了,书架塞满后,客厅墙角又堆起了两摞半人高的书堆。灰尘落在书脊的缝隙里,得用软毛刷一点点清理。她似乎不在意居住环境,沙发套洗得褪色了也没换,餐桌一角有块陈年污渍,怎么也擦不掉。
茶几上的期刊每周都换,但总是翻到特定的某一页,有时候夹着便签,有时候用铅笔画了线。阳台上养着几盆绿萝,叶子总是擦得干干净净。冰箱门上贴着一张便条,上面是手写的英文单词,每周换一个——上周是“resilience”,这周是“biodiversity”。
第三个月的一个周六,我照常去打扫。那天裴雪鸿难得在客厅,坐在沙发上看一份打印材料。我拖地拖到她脚边时,她忽然开口:“你今年大四?”
她抬眼看了看我,那眼神很平静,像在打量一件物品。然后她点了点头:“哦。”
她继续看她的材料。我继续拖地。拖把摩擦地板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响。
那天走的时候,陈姐递给我信封时多说了一句:“裴老师问你是不是每周都来得很准时。”
我试过一次。那天裴雪鸿书房的门虚掩着,我端着一盘苹果站在门外,听见里面在开视频会议。全英文,语速很快,夹杂着“沉积物”“氮循环”“模型校准”这些词。我在门口站了十分钟,最后把苹果放回了冰箱。
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,信封里的钱会多两百。陈姐解释说:“裴老师说月底大扫除辛苦,加点辛苦费。”
七百块。我全部存进了一张不用的银行卡里。卡是大学时办的,余额短信提醒早就关了。我计划着,等攒够了钱,就租一个离市图书馆更近的房子,这样省下来的通勤时间可以多做两套真题。
北理大环境学院去年的复试线是三百六十九。我的模拟考成绩在三百六十五到三百七之间波动,像心电图一样起伏不定。
那个周六我照常去裴雪鸿家。一进门就看见客厅角落里多了棵小小的圣诞树,大概一米高,上面挂着零星的几个彩球。树下放着几个包装好的礼盒。
“下周裴老师生日。”陈姐一边帮我拿围裙一边说,“几个学生要来。你今天把玻璃都擦一遍,特别是阳台推拉门。”
我擦玻璃的时候格外用力。冬日的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照进来,在地板上投出菱形的光斑。书房里隐约传来说话声,门没关严。
“基本还是去年的阵容,秦老、宋教授、高院长,加上您。但高院长说那天可能有校务会,问要不要让严老师替补。”
严老师。我听过这个名字。环境学院的官网上有他的介绍——严知行,副教授,研究方向是水污染控制。他是裴雪鸿带出来的第一批博士之一。
那天离开时,雪下大了。陈姐破例送我到单元门口,递给我一个保温袋:“裴老师让给你的,说天冷。”
公交车在雪地里慢慢开。我捧着豆浆,看窗外掠过的街道和行人。忽然想起我爸常说的话:“人情就像存钱,平时多存点,急用的时候才能取出来。”
更不知道,如果真以考生的身份站到裴雪鸿面前,她会不会从这单薄的账户里取出哪怕一丁点关照。
我只希望,如果真有那一天,她不要认出我是那个每周来她家打扫卫生的、几乎陌生的远房侄女。
“那你稳了啊!”他的声音里透着兴奋,“赶紧给你姑妈打电话!问问排名!问问复试考什么!”
“那你问问你姑妈能不能内部查查!”他的语气又急了,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!”
“我报的是北理大环境学院。”我一口气说完,“想问您……知不知道复试通知大概什么时候发?”
那天下午陈姐不在,房子里只有我和裴雪鸿。三点多,书房传来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。我犹豫了一下,过去敲门。
“不用。”她直起身时,手里那叠纸最上面一页的标题正好对着我——《北城理工大学环境学院2025年硕士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(征求意见稿)》。
要求准备的材料列了一大串,最后一条是:“请自备个人简历八份,面试时提交。”
“简历!简历好好写!把给你姑妈打扫卫生的事写进去!这最能体现你踏实肯干!”
“你懂什么!”他打断我,“听我的!你这孩子就是太老实!你每周都去,你姑妈对你印象肯定不差。面试时她要认出你,这就是缘分,是加分项!”
做简历时,我在“社会实践”那一栏停了很久。最后写下:“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,定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。”
那天陈姐请假,裴雪鸿要去学校开一天的会。她出门前给了我新任务:“书房需要彻底清洁,你今天可以进去打扫。注意,书桌和茶几上的文件、书籍不要动,只清洁表面。”
房间比我想象的还小。三面墙都是书架,塞得满满当当。窗边是一张不大的书桌,堆着高高的论文和资料。我小心翼翼地擦书架玻璃,看见许多书脊上都印着“裴雪鸿”三个字。
擦到第二排书架中间时,我看见一个木质相框。里面是张合影,七八个穿学位服的年轻人围着笑容温和的裴雪鸿。照片下方有一行小字:“2018届硕士毕业留念”。
阳光斜射进来,照在书桌一角的一叠文件上。最上面是个浅蓝色的文件夹,侧面标签打印着:“2025硕士复试-初筛材料”。
我知道,如果翻开,可能会看到复试名单。可能会看到我的名字,看到其他考生的分数和背景。
拖把头在文件夹旁边的地板上划过。我起身去洗拖把,回来时发现文件夹的位置好像挪动了一点。可能是我刚才不小心碰到的。它现在斜靠在另一摞书上,封口松了,露出里面打印纸的一角。
我蹲下来,用半干的抹布,小心地把那个蓝色文件夹推回原来的位置,摆正,让它的边缘和桌沿平行。
那天我三点就走了。在家属院门口碰见裴雪鸿回来。她提着公文包,身边跟着个四十岁左右、戴黑框眼镜的男人。两人在讨论什么“面试评分标准”,看见我时停了。
裴雪鸿点了下头,对旁边的男人说:“严老师,这是我亲戚家的孩子,苏晚,每周来帮忙做点家务。”
我没来得及回答,裴雪鸿接了过去:“她报了我们学院。初试过线了,在等复试。”
他们往家属院里走,我往公交站走。转身时,隐约听见严教授压低的声音:“裴老师,您这亲戚的孩子要是进了复试,我们这边是不是要……”
他拖个大行李箱,直接找到我租的房子。那是个十五平米的小单间,月租一千二,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公用的。
“这地方能住人?”他一进门就皱眉,“我在你考场附近订了酒店,这两天搬过去。”
他打开行李箱,里面是两套新衣服:“这套正式的面试穿,这套平时穿。都是商场买的,别给你姑妈丢脸。”
他的动作顿了顿:“去坐了坐,带了点老家的特产。怎么了?亲戚走动不正常吗?”
“我怎么了?”他的声音尖利起来,“我是你爸!你知道现在考研多难吗?三百七十一分!就比线高两分!那些高三四分最后被刷下去的多了去了!你不找关系,别人都在找!”
我们大吵了一架。吵了什么记不清了,只记得最后他指着我,声音发抖:“你清高!你了不起!那你就全靠自己考!看你考不考得上!”
复试前三天,学院网站更新了通知,加了一条:“面试将分为A、B两组同时进行,考生分组于面试当天现场抽签决定。”
那晚我做了个混乱的梦。梦见自己站在空荡荡的面试室,对面坐着几团模糊的影子。我递上简历,他们看了一眼就扔在地上:“一个打扫卫生的,也配来考研?”
陈姐发来的微信:“裴老师让我告诉你,本周六(4月19日)上午她有安排,你不用过来打扫了。面试加油。”
这两个信息在我脑子里转,引出一个我不敢细想的问题:如果她知道我那天面试,如果她知道我每周六都去她家,如果她特意把面试安排在周六——
“来送点东西。”我递给她一个纸袋,“老家寄来的新茶,给姑妈的。明天我……有事,可能来不了。”
陈姐接过纸袋,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:“裴老师明天也不在家。她要去学院,开一天的会。”
我想问陈姐知不知道明天开什么会。想问抽签的细节。想问裴雪鸿最近有没有提起过我。
那晚我最后一次核对材料。八份简历,成绩单,身份证,准考证,证书复印件。把它们整齐地码进透明文件袋,塞进背包最外面的夹层。
对着洗手间模糊的镜子练习微笑时,忽然想起,过去一年的每个周六早晨,我也是这样准备出门。只是目的地从裴雪鸿家那栋红砖楼,变成了环境学院那幢灰色的水泥楼。
收拾背包时,我犹豫了一下,把那双半旧的橡胶手套也塞了进去。没什么理由,只是一种习惯。
公交车需要换乘一次,总共五十分钟车程。我戴上耳机,里面是昨晚录的英语问答练习。声音是我自己的,但听起来陌生,像另一个人。
我站在509会议室门口时,八点四十五分。走廊里已经有十几个考生。有人小声背英文,有人反复翻笔记。空气绷得很紧。
我找了个靠墙的角落坐下,把背包放在膝盖上。橡胶手套在包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,我下意识地把它往深处塞了塞。
“现在公布分组抽签结果。念到名字的同学记住组别。A组在509室面,B组在斜对面的511室。”
九点整,会议室门开了。第一个考生走进去。门关上的瞬间,我瞥见里面是张长条会议桌,对面坐着五个人影。
等待的时间被拉得很长。第二个考生进去时,我隐约听见英文提问。第三个考生进去前不停抖腿,出来时脸色惨白。
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前最后一瞬,忽然想起每个周六推开裴雪鸿家单元门的感觉。
会议室比想象的小。窗户朝东,晨光斜射进来,在深色会议桌中央投下一道光带。
我几乎立刻认出了最左边的严知行教授——那天在家属院门口见过。他今天穿浅蓝色衬衫,朝我微微点头。
最右边还有一位,看起来最年轻,约莫三十五岁,戴无框眼镜,双手交叉放在桌上。
我把八份简历依次递到每位考官面前。最年轻的那位接过时说了声“谢谢”,声音很平静。
我开始背那篇演练过无数遍的英文自我介绍。声音还算平稳,至少我自己听不出抖。
白发老教授推了推眼镜:“你本科阶段在滨城环境监测站实习过,主要参与什么项目?”
严教授开口了。他问了个具体的专业问题:“谈谈你对微塑料在淡水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转化机制的理解。”
我尽力把本科所学和近期看的文献结合起来回答。说到一半时,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。
大脑飞速搜索。裴雪鸿的书房。那张书桌的笔筒里,就有一支一模一样的笔。有一次我擦桌子时,那支笔滚到地上,我小心捡起来放回去。笔杆上有个很小的、独特的logo,当时没细看。
如果是普通款式就算了。但那支笔的设计很特别,我在别处没见过。而且,裴雪鸿笔筒里的笔大多是黑色或深蓝色,只有那一支是墨绿镶银。
白发老教授推了推眼镜,没有回应。他只是再次低下头,看我简历的眼神变得有些难以捉摸。
过去一年的每个周六清晨,我拎着水桶和抹布,站在那栋爬满枯藤的红砖楼前按门铃的画面,不受控制地涌了进来。
女教授低下头,在我的简历上写了很长一段评语。写完后,她抬起头,深深看了我一眼。那眼神很复杂,像在审视,又像在评估什么难以量化的东西。
“好的,面试到此结束。你可以离开了。最终结果三个工作日内会在学院官网公布。”
我就会在她面前,在我的研究生复试现场,在递上写着“苏建国之女”的简历之后。
她正在和一位女老师说话,手里拿着个文件夹。我下意识侧身,躲到一根承重柱后面。
“不过来了,学校有个紧急会议要她主持。”陈姐回答,“严老师不是在509了吗?裴老师说,有他在就可以了。”
“那倒也是。”女老师点头,翻开文件夹看了看,“严教授是她带出来的第一批博士,面试的标准和尺度,肯定都清楚。”
我忽然想起书房里那张合影——2018届毕业生。严教授看起来四十多岁,博士毕业至少是十几年前。所以他不止是她的学生,更是早期弟子,堪称“开山大弟子”一样的存在。
那么,今天面试我的五位考官中,至少有一位,是裴雪鸿学术血脉的直系传承者。
最年轻的那位——周副教授,简介最后一行:“师从裴雪鸿教授,2015年获博士学位。”
严知行教授——简介里同样写着:“师从裴雪鸿教授,2008年获博士学位。”
她的简介里,有一行这样的描述:“2012年至2015年,于裴雪鸿教授课题组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”
我再仔细看高副教授的简介。在密密麻麻的成果列表中间,发现了一句:“曾作为主要成员,参与裴雪鸿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。”
秦教授呢?我重新仔细读他那长得多的简介。在最后一段,看到一句:“长期与裴雪鸿教授团队保持学术合作,共同指导博士生三名。”
其中四个,都与那个我每周去为她打扫房间的女人,有直接或极其紧密的学术关联。
严教授肯定知道。他不仅在家属院门口见过我,知道我是“亲戚家的孩子”。他今天更是特意问了我父亲的名字,特意提起了裴雪鸿。
周副教授呢?他特意提到我本科的科研实践,还低声问秦教授裴雪鸿是否做过联合指导。
秦教授呢?他看起来最和蔼,但最后那个关于亲戚关系的、最关键的问题,是他问出的吗?不,是宋教授问的。但秦教授显然知情。
没有人知道,我把每个月那五百或七百元“劳务费”悄悄存起来,梦想着租一个离知识更近的容身之所。
在花坛边坐了二十分钟,我看着其他考生陆续从楼里出来。有人兴奋地打电话,声音雀跃。有人垂头丧气,步履沉重。
我看见严教授和一位年轻助教边走边聊,经过花坛时,他看见了我。他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,但没停留,也没说话,继续往前走。
我不知道自己还想做什么。也许是想看看511会议室什么样,B组的考官又是谁。也许,只是内心深处那份强烈的不甘心,驱使着我的脚步。
四楼的走廊已经空荡荡,面试全结束了。509和511的门都开着,保洁阿姨正在里面打扫。
“……没有。”我顿了顿,“阿姨,请问今天在这间教室面试的老师们,您认识吗?”
会议桌上有几个用过的一次性纸杯。其中一个杯壁上,印着一圈浅浅的口红印。说明B组也有女考官。
“A组(严负责):苏(亲)、张(382)、刘(380)…B组(宋负责):陈(381)、王(379)…裴院长交代:一切按既定章程与标准执行,无需特殊考虑。”
窗外射进来的阳光,正好落在“苏(亲)”这两个字上,落在“无需特殊考虑”这六个字上。
还是说,正因为标了“亲戚”身份,反而要更严格地审视,以证明全过程的绝对公正?
这张纸没写任何结果,它只揭示了一个冰冷的事实:在考官们眼里,我是“苏(亲)”,而不是“苏(371)”。
宋教授站在他身后,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,随即移向我紧握背包带子的手——那双橡胶手套的一角,从背包侧袋露了出来。
宋教授也走进来,她拿起桌上的水壶,给自己倒了杯水。喝了一口后,她看向我。
“哦。”她点点头,又喝了口水,“裴老师家虽然不大,打扫起来也挺费工夫吧。”
办公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。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,在规律地走动,发出咔、咔的轻响。
她放下水杯,走到我面前。她的眼神锐利如刀,仿佛要穿透我的皮肤,看清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
“因为她不想让你为难,也不想让自己为难。”宋教授的声音很清晰,每个字都敲在我耳膜上,“她让我和严老师来,是因为我们都是她一手带出来的学生。我们最清楚她的学术标准,也最明白她为人处世的原则。”
“裴老师的原则是,学术归学术,人情归人情。所以,她从来不收任何亲戚、朋友的孩子进自己的课题组。一个都没有。”
“但你是第一个。”宋教授说,“第一个以亲戚身份,来报考她所在学院的硕士生。所以她很为难。不招,家族人情上或许说不过去。招,就打破了她坚持了近三十年的规矩。”
“所以她让你每周去她家。她想亲眼看一看,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。是想真心实意做科研,还是仅仅想借她这块‘跳板’。”
“你今天面试的表现,可圈可点。”宋教授说,“专业基础回答得比较扎实,英语口语也流畅。初试三百七十一分,过了线。”
“但你知道,B组有个考生初试三百八十二分吗?还有一个,本科就以第一作者发过SCI论文。”
“今年全院通过统考招的名额,非常有限。”严教授的声音响起,“我们这组,和B组,最终可能各自只有一个录取名额。”
“面试成绩,在总评里占百分之五十的权重。”严教授说,“如果你的面试表现足够好,综合评分就能占优势。”
“我们刚刚已经给你的面试打了分。”宋教授从桌面上拿起一张评分表,“但最终的录取结果,需要综合初试和面试分数,加权计算才能确定。同时,也需要……”
因为严教授和宋教授都是她的学生,他们必定会尊重她的意见。而高副教授是她的重要合作者,同样会充分考虑她的态度。周副教授是她的年轻弟子,更不用说。
“她今天没有出现,是因为她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。”严教授说,“她需要时间。”
口袋里的那张纸,坚硬的折角硌着我的大腿。我伸手进去,指尖触碰到那行冰冷的字迹:“裴院长交代:一切按既定章程与标准执行,无需特殊考虑。”
宋教授的回应紧接着响起:“那她今晚肯定会找我们要详细的面试记录。你把我和高老师上午记的评估笔记整理好,一并发给她。她知道苏晚每周去打扫卫生的事吗?”
“陈姐应该汇报过。”宋教授的声音很平静,“但她从未在我们面前主动提起过。刚才那孩子自己承认了。”
“怎么一直不回消息?到底怎么样了?我给你姑妈打电话她一直不接!你快点联系她问问情况啊!”
车辆启动,缓缓驶离路边。我回过头,透过布满灰尘的车窗,再次看向那扇五楼的窗户。
我看着窗外掠过的商铺、行人、高架桥。这座城市,我待了将近一年。每周六穿越半个城区去做保洁。每天泡在图书馆或出租屋里刷题。住着月租一千二、只有十五平米的小房间。吃着最简单、最便宜的饭菜。
还是因为,她终于不得不直面这个困扰了她一年的难题——是否要为自己远房亲戚的孩子,破一次例?
我甚至不知道,今晚她看完录像后,指间轻轻落下的一笔,会为我勾勒出怎样的未来。
听筒里传来的女声,平静,清晰,带着一种我熟悉的、属于实验室和学术报告厅的冷静质感。